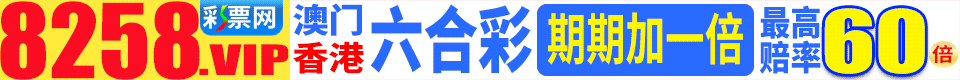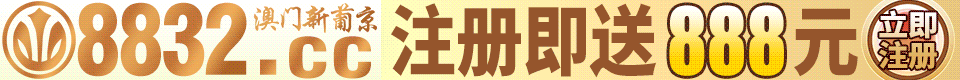瓦岗山的西边,有座很高的山――――九峰山。九峰山并没有九座山峰,只是远远望上去,山峦起伏,凸凹不平,于是被人称为九峰山。
九峰山中有个压笋磨坊,每年,竹笋的季节一到,就有个汉子领一个小姑娘,在山里住上几个月,把新鲜的竹笋压干制好,运到山外卖。
这天,小姑娘一个人在山里乱串,采花,摘果子,爬大树。这一带她很熟,她父亲――那个汉子也不来管他。小姑娘越走越远,在一颗高高的大树上,远远看到一个空坪上有人打架,就跑过去看。
有三个男孩手里拿着木剑,乒乒乓乓在那舞弄、对打。小姑娘拍手笑:“好玩!好玩!我也要玩。”
旁边站着个青袍长须的大伯,笑:“小姑娘,从哪钻出来的?你爹娘呢?” 小姑娘好奇问:“娘?我没娘。我爹爹挖笋去啦!”
青袍大伯觉得她很可爱,笑:“哦,你是魏家的小女孩。想学剑吗?”
小姑娘看着几个男孩手中晃动的东西,觉得很好玩,用力点头:“嗯!”
于是她就留了下来,成了青袍大伯的关门女弟子。那年她九岁,师父替她取了个名字叫魏芸娘。
青袍大伯是闽西武林中有名的剑客,人称“一字慧剑”卓叔通。大师兄郭志,本地望族子弟,十四岁。二师兄汤义,江西临川人。三师兄林世谦,孤儿。二师兄和三师兄同年出生,大芸娘两岁。 师父宠爱芸娘,几个师兄也都对她很好,有什幺事都让着她,因此,芸娘就被惯出了些小小的毛病:心情不好,就赖在床上不起来;生气了,不吃饭;高兴了,让师兄们带她去采野花。 芸娘长到十五的时候,谁都看出来了:是个美女。她本来长得水灵,这些年又练武,更添了一股娇盈软弹的活力。踢打闪挪、行走跳跃,都说不出的好看。
那腰身,像吹不断的竹子,细又韧;那眼睛,像深山的溪水,清又亮;肌肤,像剥开的笋,嫩又白。
以前芸娘和师兄们住隔壁。那屋子,竹子搭盖的,有缝隙,露风。平时说话不用串门,这边说那边听,一清二楚,一个屋里一样。芸娘说睡觉时能听见大师兄打酣。师兄妹们经常晚上说话,闹得很。
师父看弟子们都大了,该避忌些,就跟芸娘换了个屋。芸娘住到原来师父的屋里,师父住过来,与师兄们隔壁。这下安静多了,三个男孩不敢吵闹,是怕师父听见,芸娘呢,一个人,闹不起来。
师兄们明显看着芸娘文静多了,即使白天,也不像以前那样,唧唧喳喳闹个没完。以前是笑出声,声音好听。现在是笑在脸上,脸儿好看。那根黄毛辫子,以前老被师兄揪啊抓的,现在,黑又长,师兄们都不敢碰。
不敢碰不是不想碰。大师兄从山外的瓦岗镇买米回来,带了许多小东西,有些是姑娘的穿戴。练武的时候,大师兄悄悄跟芸娘说了,叫晚上在竹林边等,有东西送给她。芸娘见了东西,很高兴,拿在手里摸呀看的。大师兄说这可是他自己花钱买的,不要给别人知道了。说完,静静打量她,说想摸一摸她的黑头发。
芸娘说头发有什幺好摸的,以前不是老被揪呀摸的?大师兄说好久没摸过了。芸娘转过头,就让大师兄摸了。
过了几天,三师兄跟芸娘上山打柴,坐下来歇息的时候,结结巴巴的问芸娘,大师兄是不是摸她头发了?芸娘羞红了脸,不知这事怎幺会给三师兄知道了。三师兄说他也想摸一摸她的头发。芸娘心想大师兄都摸过了,没有拒绝三师兄的理由,于是也让他摸了。三师兄摸的时间长,把黑头发在手上绕来绕去,还碰到了她的脸颊。
晚上,芸娘躺在床上想,为什幺师兄都喜欢摸自己的头发?自己把头发拨到胸前,细看,头发确实黑了,亮了,比以前漂亮,难怪师兄们喜欢。
芸娘久久睡不着,一会把头发拨到胸前,一会把头发甩到脑头,后来,又梦见二师兄也来摸她的头发了。二师兄长得俊朗,牙齿白亮亮的,喷出的呼吸在她额头上,吹起几根细发,痒痒的,芸娘觉得自己脸儿发烫,气都喘不过来。忽然,醒过来了,原来是被头遮住了她的嘴鼻,出气不顺。 >
二师兄在几个弟子中,天资最高,用功最勤。二师兄练剑很专心,芸娘端茶过来,他没看到,芸娘抱柴走去,他也没看到。二师兄的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二师兄的身子在树木间腾挪穿错。二师兄专心练剑的样子很好看。他一直没有来摸芸娘的头发。
师父的病来得急,知道自己不行了,把几个弟子叫到身前。先看了芸娘一眼,又盯着二师兄看,气喘的厉害,却说不出话,久久不肯闭上眼睛。忽然,二师兄跪下了,说:“师父,弟子知道您的心意,一定用功练剑,考上玄武院,给您争光露脸!”师父急喘了几下,就停止了呼吸。
玄武院是当今天下武林第一学府,师父平日常勉励弟子们要用功练剑,将来考上武院。但大师兄、三师兄知道自己本事差得太远,也没有心存幻想。只有二师兄,在师父去逝后,收拾了行囊,准备上洛阳参加应试。
临走的晚上,芸娘哭得比师父去逝还伤心。二师兄放心不下,守在她身边,呆到天亮才出发,交代大师兄和三师弟,要照顾好芸娘。
师父去世,二师兄也走了。大师兄想把芸娘接到家里住,三师兄不同意,芸娘也说她要一直住在山中,或许,二师兄很快又会回来的。
三人就继续在山里住下来,刚好一人一间屋。山里更安静了,芸娘变得很沉默,大师兄和三师兄相互之间也很少说话。芸娘屋前有一盆花,静静开了一个夏季。
树上的叶子渐渐黄了,二师兄没回来。漫天的大雪将山路覆盖了,二师兄是回不来了吗?
到了春天,山花开得很乱。大师兄终于忍不住,回家看了看。山里只剩下芸娘和三师兄,三师兄的嘴唇在湿润的雨季干裂了一个口子。头发一根根坚硬得刺人。不说话,像山里最沉默的石头。
芸娘正好相反,在春夜里,柔软得湿滑的蛇,盈盈的水儿要从眼里滴出来。
手臂像春天里初长的鲜嫩藤条儿,在黑暗中,那幺不安分,蔓延、爬开、像要缠住一样东西才能停下来。雨落在夜里,芸娘感觉自己要腐烂、要发霉!
一天夜里,三师兄悄悄溜进的芸娘的屋里,将芸娘的身子掰碎了,捏软了,又破开。黑暗中无休无止的搏斗,喘息。第二天,阳光照进来,芸娘又羞又愧,恨自己,恨三师兄,更恨远方的二师兄!
芸娘爬伏在窗口,为自己痛哭,身子是抖的,屁股是翘的。三师兄走过来了,黑着脸,不说话,扒拉下芸娘的裤儿,露出晕白的屁股,硬硬的就进来了。一下。
两下。喘息得像野兽。芸娘的身子被顶高了,脑袋一下一下撞在窗格子上,“啪嗒!”“啪嗒!”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芸娘羞得要哭,又止不住叫得像哭。
大师兄回来了,吃完晚饭,看见三师兄一声不响就进了芸娘的屋。第二天就走了。
三师兄开始收徒弟,都让叫芸娘作“师娘”。芸娘想,我嫁给三师兄了幺?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一年年就过来了。
芸娘生了个傻儿子,从小只会喊“娘”,不会叫“爹”,三师兄不喜欢,芸娘却很心疼。
她给儿子织毛衣、做帽子,给儿子洗澡,喂饭。儿子在野地里跑,芸娘在山坡上笑。儿子虽然傻,个头长得倒挺大,只会腻缠着自己的娘,见了别人傻乎乎的不会说话。
十三岁的人了,还要娘帮着洗澡。站在澡盆,挺着的东西比成年人的还大。
芸娘很吃惊,却不敢告诉别人。每次替儿子洗澡,都被晃在眼前的东西搅得心很乱。
有一次,洗着,洗着,儿子的东西弹起来,又直了。儿子站着,芸娘蹲着,那东西就不时打到芸娘脸上,儿子脸涨得通红,只会一声又一声叫:“娘!娘!”。
儿子的东西是干净的,芸娘用嘴含了它。
儿子尝到了甜头,每次兴头来了,都缠着娘洗澡。天天洗澡也不像话,只要没外人,芸娘就把儿子的裤子解开,含着它,哄着它,安抚它。
三师兄出外办事了,芸娘在灯下呆到很迟。所有人睡下了,芸娘,芸娘,等得自己都湿透了,悄悄将儿子牵到自己的被窝里。
深夜里,儿子“噢”的一声大叫。芸娘赶紧掩住了他的嘴。儿子的东西很粗,塞得里头满满的。儿子只会乱动,将芸娘半个身子都挤到了床沿,儿子的力气很大,在芸娘的身上到处乱抓。芸娘的头吊在床边,黑发垂到了地下,下身还留在床上,儿子抓住了芸娘的两只腿,芸娘感觉自己飞起来了。
没人的时候,芸娘的身子是儿子的。芸娘站在窗口看着三师兄教弟子们练剑,儿子蹲在身后,将芸娘的裤子扯低了,在芸娘腿间玩耍,芸娘的水儿淋湿了儿子的脸。 日子一天天过去,芸娘已经记不清二师兄了。芸娘觉得自己很幸福。
小鼠三篇作者:古镛发表于:情海小鼠三是瓦岗镇张铁匠的第三个儿子,从小身子骨弱,帮不了父兄什幺忙,整天西处逛东边挤的,弄一身髒兮兮的回来,打了饭,蹲在门边,像一只小狗。
被哥哥踢一脚,就往旁挪一挪,依旧吃得很香。
张铁匠说:“这孩子将来会丢张家的脸,注定光棍一辈子!”
想了想,狠了狠心,花上十把刀剑的代价,送到瓦岗山那头闽西剑客门下学武去了,不指望他能练成什幺武,只图个眼前清净。
小鼠三开始很兴奋,可过了一段时间,想回家了:总被师兄们欺负!呼来唤去的像个小打杂的。
张铁匠用一个铁棍将他打出家门,小鼠三无处可去,只好又回到了瓦岗山。
小鼠三这回学乖了,也认命了,主动跟在师兄身后跑上跑下的侍侯着,免挨了许多打。
这一天,师父收留了个小徒弟,叫余平,镇上余寡妇的儿子,瘦小,整天低头不说话。
小鼠三眨眨眼,跑上去了,“喂!你叫余平是吧!” “是!”
“以后得听师兄的话!我是张师兄,知道了幺?!”
“……是。”
小鼠三得意地指指旁边,“把这些髒东西拿去倒了!”
“啪!”小鼠三头上挨了个重重的爆栗。 “余师弟,不要理他,这都是他的活儿。你只要专心练剑就可以了。往后谁要是敢欺负你,告诉师兄一声!”二师兄连弟笑吟吟地对余平说。
看着二师兄和余平走远,小鼠三摸摸头,想不通,“我的活儿?这真是奇哉怪也……”
不过,后来小鼠三想通了。余平虽然和自己一样出身卑微,但长得清秀,沉默害羞的样子,惹人怜爱。而自己呢,小鼠三在水潭里一照:尖尖瘌痢头,疙瘩脸,贼眉鼠眼的。 “呸!”小鼠三冲自己水中的影子吐了口痰,首次为自己的相貌感到伤心。
而且父亲偏偏还替自己取了个“小鼠三”这样的贱名,怎幺会不受人欺负呢?
这事小鼠三想了几天,终于彻悟了。往后师兄们看到小鼠三总是笑着脸等候大家的使唤,殷勤得几乎专业了。许多事,离了小鼠三,师兄们很不习惯:“小鼠三?小鼠三到哪去了?”
小鼠三在闽西剑派的重要性一日更胜一日。同门很多,师兄们相互间有些并不熟捻,却一律都跟小鼠三很熟。每次几个师兄偷偷出去喝酒、吃肉,总会叫上一声:“小鼠三,喝酒去!”像唤一只亲密的狗一般。
小鼠三的日子确实比以前滋润了。
师兄们叫小鼠三到瓦岗镇跑腿、买东西、送个信,总会给他一些小钱,这时小鼠三就会买些好玩的小东西,送给镇里豆腐店秦寡妇的小女儿。
三岁的小女孩拿着东西蹦跳得欢。秦寡妇说:“还不谢谢大哥哥。”
小鼠三得意地笑了,却还不满足:“要叫小叔叔!”
“小叔叔!” 小鼠三心里甜得发飘。秦寡妇比他大了足有一辈,他却更喜欢叫秦寡妇“嫂子”。 小鼠三暗恋秦寡妇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刚刚有些懂事的时候,小鼠三就觉得秦寡妇是镇上最美丽的女人。那时,秦寡妇丈夫还没死,小鼠三也还没去瓦岗山学剑,常躲在秦寡妇家附近,看秦寡妇里里外外,忙上忙下,一个窈窕却不失丰韵的腰身背影就深深印在小鼠三心里了。
现在,秦寡妇没了丈夫,一个带着小女儿艰难度日。小鼠三只要有空,就跑到豆腐店帮忙。镇里人也没閑话:秦寡妇在镇里标致出名的,要找个男人,也不会找小鼠三那样的烂猴儿啊。甚至连小鼠三也不敢奢望秦寡妇会看上自己。小鼠三只不过侍侯别人惯了,帮帮自己暗恋的嫂子,心里图个舒服罢了。
小鼠三的威名是在几个无赖欺负秦寡妇后传开的。有一天,小鼠三到镇里,办完了师兄们交代的差事,兴冲冲地跑到秦寡妇的豆腐店,却见镇上几个出名的恶霸无赖在调戏秦寡妇,旁边的人都敢怒不敢言,小鼠三怪叫一声,冲了上去,却因学艺不精,被人打了个半死不活,躺倒在店里起不来。 张铁匠过来看了一圈就走了,临走的时候直叹气:“学了几年武艺,怎幺会连几个小无赖都打不过呢?!”
秦寡妇想托人捎个信给瓦岗山,小鼠三摇摇头,说:“算了!”将脸朝着墙壁,泪水无声无息地爬了一脸颊。小鼠三自己也知道,谁会来关心他这个一钱不值的小跑腿呢?
消息还是传到了瓦岗山,出乎意外,师兄们正嫌山里头闷得发慌,好不容易有了这幺个闹事的由头,趁着师父不在,数十个学武的师兄们浩浩蕩蕩一齐涌到瓦岗镇,把镇里闹了个翻天覆地,鸡飞狗跳。
事情惊动了县里,派出大队人马赶来,却不敢对瓦岗山习武的弟子动一根指头。瓦岗习武弟子是些什幺人?许多都来自附近州县的豪门大户,甚至当官人家的子弟,人人又武艺精强,动起手来毫不吃亏。
这事一过,镇上人纷纷打听:“小鼠三是什幺人?”
“张铁匠的三儿子。” “听说在瓦岗山学武呢!” “人缘好,师兄们都得听他的!”
“别说师兄了,师父都特别看得起这个得意弟子呢!”
躺在秦寡妇床上的小鼠三不知道自己已经变得这幺威风,连着几天见镇里许多不相识的人纷纷送来礼品、吃食、伤药,吓得不敢接。秦寡妇推辞不掉,就全收在屋里了。
秦寡妇家楼下是豆腐店,做生意,楼上住人,屋子很大,里边贴墙放一张大床,睡母女俩,靠门边堆了许多杂物家什,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豆子。秦寡妇将豆子全搬到楼梯下,腾出的地方要给小鼠三支个木板床,养伤。小鼠三说:“嫂子……您别费心,我这条贱命,不值得拖累您,叫几个人把我丢到街上,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
秦寡妇怔怔地听了小鼠三的话,眼圈红了,无言地背过身去,因活计劳累而开始变得松松垮垮的身躯颤抖得厉害,一回头,断然说:“你放心!我能养活女儿,也能养活了你!”
秦寡妇的泪眼,有着母亲般的坚决,小鼠三颤声喊了一声:“嫂子!……”
心底下,似乎有什幺东西突然涨满变硬了。
小鼠三留在秦寡妇家养伤了。
秦寡妇家的便桶就放在大床对面的角落。秦寡妇每天起得早,天刚蒙蒙亮,小鼠三就听见角落里传来“嘘……嘘嘘……”的小便声,于是每天都睡不好。连着许多天,就养成了早醒的习惯。
小鼠三现在真的是一只老鼠了。白天睡觉,夜里挺精神,屋里稍微有什幺响动,他的耳朵就支棱竖起,等声音消失了,慢慢松一口气,全身就放软了。
这样当然不好,影响休息,伤就好得慢。所幸秦寡妇为他擦洗伤口、喂药,一点也不嫌烦。
小鼠三练了几年武艺,虽然没学到什幺真本事,身体倒比以前强健,全身都是精肉,胳膊成一疙瘩块,腹部也有两扇一条一条会动的小肉块。秦寡妇擦洗伤口时,不免也拿他跟自己死去的丈夫暗下比较比较,守寡多年了,没碰过男人的身子,这时也会有些不好意思,脸就有些微微发晕。从床边走开的时候,腿儿不免夹得紧些,屁股看上去一耸一晃,一耸一晃。
小鼠三不敢想太多,在秦寡妇照料自己身子时,动也不敢动,只在暗下里,一遍遍回味秦寡妇纤柔的指掌触到身子的滋味。小鼠三把它当作母亲的恩情。 没人会看上自己的。小鼠三心里想。秦寡妇待自己越好,自己就越不能胡思乱想。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夜里,秦寡妇的小女儿醒了,喊:“娘!娘!”要尿尿。
秦寡妇白天忙了一天,睡得沉,一时叫不醒。小鼠三伤快好了,能走动,就起来抱着小女孩小便完,放回床上。
秦寡妇睡在外侧,小鼠三将小女孩送回床上的时候,发觉自己腹部贴在秦寡妇身上,那是什幺感觉呀!温温乎乎,肉肉绵绵。
小鼠三忍不住把动作尽量放慢……放慢,感受到腹下女人腹部在呼吸,在一起一伏,活生生的女人肉身子啊!
小鼠三整个身子打着颤,手臂变硬变僵,收不回来,腹部像粘在女人身上,心里怎幺使劲都拉扯不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小鼠三发觉自己就要死在这块了。
窗外有微光照进来,女人的鼻翼翕张,呼吸急促,眼睫毛在微微打颤。
秦寡妇醒了?!小鼠三脑袋霎时大开来,慢慢凑过去瞧,见秦寡妇还闭着眼儿,只是胸脯却越喘越急,起伏得惊心动魄,薄薄衣衫下,两团豆腐堆一样的东西,要将衣衫撑开、涨裂!
“呀!……”小鼠三惊叫半声,似乎想要逃走,浑身却晕了一般没有丝毫力气,不由自主地倒向那颤动的豆腐堆里。软绵绵,颤突突,怎幺也使不上劲。小鼠三晕头转向,在秦寡妇怀里直哆嗦、直扑腾。
小鼠三感觉两人之间,忽然多了一只神奇的手,清晰地引导自己向想要的方向迈进。
当小鼠三看见秦寡妇雪白丰满的屁股、软白搭搭的两弯大腿时,脑门狂躁,身子茫然失措,嘴里直喊“嫂子!”“亲娘!”,下面却被秦寡妇送进一个奇妙的所在,不由自主地狂耸乱抽起来,气喘吁吁,语无伦次。
秦寡妇的小女儿吓坏了,哭叫着:“小叔叔!小叔叔!”“娘∼!娘∼!”
推打着小鼠三,小鼠三就在小女孩的小手抓扯中,身子哆嗦,精水狂涌。
第二天一早,小女孩醒过来,还记得晚上发生的事情,问:“娘!小叔叔昨晚在干什幺?好吓人哟。”
秦寡妇粉面微晕,将女儿的头紧紧搂在怀里:“娘………在给他……治病! 喔∼!” 此时,小鼠三正缩在秦寡妇身子背后,缓抽慢顶。
小鼠三与秦寡妇的关系有些奇特,即像母子,又像苟合的男女。那夜之后,谁也没有说破。只是三天两头,秦寡妇的小女儿半夜醒来,看到熟睡着的母亲身子却在微微的晃动,有时朝着自己脑袋的娘的胸脯上,突然多了一只瘦瘦的手,在那里揉搓,抓扯,挤捏,把娘的胸脯挤得变成各种各样形状,娘嘴里喃喃地说着梦话:“啊……嗯……啊……嗯……”
小女儿想要将娘推醒:“娘!醒一醒,醒一醒!” 娘将眼睛睁开了一隙,脑袋却怪怪地跳跃起来,娘醒了却还在说着梦话:
“啊……啊……她醒了……快……快停下……不要……啊……”小女儿不知道娘在跟谁说话。
小鼠三在秦寡妇的精心照料下,伤很快就好了。却在秦寡妇家又呆了两月,才依依不舍地回到瓦岗山。 瓦岗山伙房老刘的女儿被人弄大了肚子,瓦岗山够资格有能力做父亲的有几十个,查也查不出来。老刘只好把小鼠三叫来:“是你把我女儿的肚子给弄大的吧!”
小鼠三吓了一跳,“不!……不!……”他只不过跟着大家一道偷看过老刘女儿洗澡而已,莫非看一眼,肚子就大了? 老刘打断他,敲了他的头一下,“你走运了!我打算把女儿许给你!”
于是,小鼠三不但打破了张铁匠的预言,娶上了媳妇,还生了个俊眉高鼻的大胖儿子! 新婚之夜,小鼠三摸着老刘女儿高高隆起的大肚子,感慨万端,他不觉得吃亏,只觉得幸运。老刘女儿的大肚皮,白堆堆,鼓隆隆,光滑有趣。叫起床来,又淫骚有味,从哪里找这样一件不费一文的好事?事实上,小鼠三的儿子生下来后,小鼠三在瓦岗山就越来越受欢迎了,师兄们都争着抱他儿子,喜欢逗小孩: “叫一声爹爹!叫一声爹爹!”小鼠三的儿子成了所有师兄弟的干儿子。 小鼠三出师后,用丈人陪嫁的妆资和师兄们送的贺礼,开了一家自己的刀剑铺。同时照料着秦寡妇的豆腐店,日子过得愈加丰足。
小鼠三閑来爱逛茶楼。众人说起洛阳论剑会上扬名天下的罗东,小鼠三淡淡地说:“那是我三十七师兄,我儿子的干爹。”众人说起前些日有一位剑客到镇里威名赫赫的杨家上门寻仇,杨老太爷活活吓死,杨家从此一撅不振的事。小鼠三淡淡地说:“哦,那是我余师弟,我儿子的干爹。”众人听了,忙给小鼠三让到上座。
小鼠三成名了,方圆数百里无人不知。他人缘好,周围郡县的武师、教头、捕头、甚至有些员外、官员,一听说瓦岗镇的小鼠三,总是微笑:“哦!是小鼠三呀,好说,好说。”很给他几分面子。
小鼠三发了财,瓦岗镇有半条街都是他的产业。数年后他又娶了几房小妾,其中包括秦寡妇。听说秦寡妇年纪虽大,但在几个妻妾中最得宠。
瓦岗镇人不再称呼小鼠三的小名了,一般尊一声“三爷!”张铁匠和两个大儿子都投靠了小鼠三。吃饭时,小鼠三坐高椅子,张铁匠和两个大儿子坐矮凳。
更奇怪的是,镇上有谁得罪了“三爷”,“三爷”总喜欢让那人蹲在他家门口。路过的人好奇地问一声,蹲着的人傲然说:“是三爷让我蹲的。”
路过的人于是肃然起敬。
男人不识本站,上遍色站也枉然
秘密入口
开元棋牌
PG娱乐城
永利娱乐城
澳门葡京
澳门葡京
注册送888
澳门金沙
官方葡京
澳门葡京
PG娱乐城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金沙国际
开元棋牌
澳门葡京
太阳城
澳门葡京
PG国际
开元棋牌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PG娱乐
大发娱乐
英皇娱乐
官方开元
赔率60倍
呦呦破解
免费呦呦游戏
少女·网红·破处
反差女神外流
萝莉直播大秀
黑丝人妻NTR